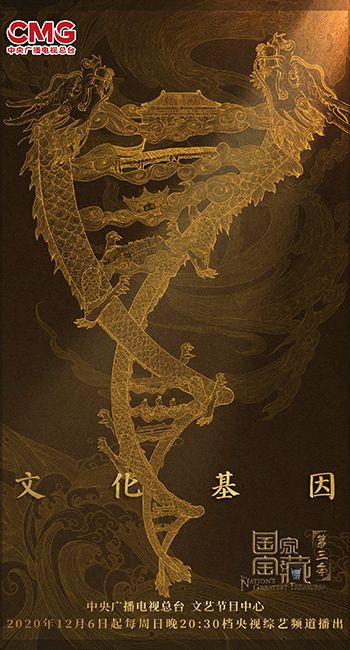宁浩:《我和我的家乡》跟每一个小人物都有关系
一直以“黑色幽默”“荒诞”“疯狂”为创作风格的宁浩,最近的作品多了些温情的底色。
---------------
外地亲戚上城里来看病,这事儿大家经常遇到,导演宁浩也遇到了。除了对疾病的忧心,亲戚还担心在北京看不起病——虽然有农村医保,但是不知道能报多少,北京是否覆盖,便不敢做手术。宁浩说,你别想后面那些问题,我们可以帮助你。
可一旦涉及金钱,平等的亲戚关系似乎多了一点亏欠,这让宁浩有点尴尬。等到做完手术,亲戚惊喜地发现医保可报销百分之八九十的费用,一下如释重负。亲戚又回到长辈的位置上,双方重新平等了。
这事对宁浩触动很大,农村医保惠及农民,“确实是政府办的硬事”。在接到《我和我的家乡》“命题小作文”任务后,宁浩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异乡人的小故事,于是就有了分单元《北京好人》。
此前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,宁浩执导的《北京你好》单元影片,以出租车司机“张北京”的视角看奥运会背景下的北京。这次葛优在《北京好人》中饰演的角色,沿用了“张北京”的名字,虽换了个职业,性格依旧吊儿郎当、不着四六,喜剧色彩颇浓。
一直以“黑色幽默”“荒诞”“疯狂”为创作风格的宁浩,最近的作品多了些温情的底色。即将上映的《我和我的家乡》,以5个具有代表性的“家乡”为蓝本,展现当地的风土人情与真情故事。作为该片总导演,宁浩总结,整体策划与出发点是3个关键词:变化、空间、小人物视角。
在筹备阶段,宁浩和张艺谋、张一白商量,要用一个主题把各个单元串在一起,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核心词——“变化”,家乡和千家万户都因为全面小康和精准扶贫而发生变化。确定主题后,如何串起来?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叙事结构是时间轴,每10年一个故事;在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中,连接线变成了5组空间概念,散落在中国版图上的东西南北中。
宁浩习惯以小人物为视角讲故事,把落点定位在“人”。“家乡和祖国这两种力量感是不一样的。提到祖国会让人们觉得很宏大,有血脉贲张和自豪的感觉,而提到家乡则特别温暖。家乡应该是更具体的关于人的描述,关乎每个个体”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从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到《我和我的家乡》,叙事落点发生怎样的变化?
宁浩:提到家乡就像想起母亲,想起家庭一样,是非常人性化、人格化的,它应该是更具体地描述“人”,以及每个个体与事情的关系。
《我和我的家乡》有几个关键词:变化,空间,还有延续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里的小人物视角,这三点是比较核心的。然后大家就开始各自领任务。我延续性地接着做北京的故事;沈腾、闫非、彭大魔都是东北人,所以他们很自然去东北,在东北体验生活,在那里进行创作。邓超、俞白眉导演的单元,俞白眉是西安人,就去了西北,在陕西进行创作。徐峥是上海人,他在千岛湖那边开始创作。只有陈思诚,他是一个东北人,但是他一跳上来就说,“我要去西南!”他自己也很想去西南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你曾说自己“习惯于在破铜烂铁里面寻找价值”,你是如何形成这样一个观察视角?
宁浩:前段时间我试着去写一些大明星、大人物,我发现特别难。我不是他们,我就没素材,我也想象不到他是怎么想问题的,我只能写那种我能理解的东西。我能理解的就是市民阶层,我拍的就是市民阶层,从自己的感触出发去做东西,我只会这一个办法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大家在提到你之前的作品时,会提到黑色幽默、多线叙事、荒诞这类关键词,为什么偏爱用荒诞或喜剧的方式讲故事?
宁浩:我觉得中国的创作者好像对这事情并不陌生,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相声基础的国家,也是有脱口秀基础的国家。我们一直都渴望轻松的视角和生活,我们有这样的土壤和思维方法,所以你看中国的喜剧明星特别多,生旦净末丑里,生角少一点,丑角反倒是蛮多的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这部电影有喜剧的外壳,内里包含许多对现实的思考,你在平时创作的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坚持吗?
宁浩:我没有故意思考现实,也没有故意在做喜剧,我其实就是在对真实负责。“什么是真实的东西?”你要是这么想问题的话,肯定会在看到事情表面的时候,愿意去想它的原因,它到底为什么这样。想多了自然会带出一点表面以下的东西,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你曾说“作为一个创作者,最难的是保证永远有话要说”,你如何保证这种源源不断的创造力?
宁浩:一个是有话要说,另一个是要少说废话,虽然我也说了不少废话,但我觉得重点是你在关注什么事情。比方说这个世界真的在发生什么?它的真相是什么?
我在研究我的下一个片子,抓了一个题材——代孕。我觉得代孕这件事情是一个新的问题,这个问题带来了对很多环节的重新思考,包括伦理,包括法制,很多问题都要与之相配套。这种事情就是我感兴趣的事情,去观察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。(实习生 余冰?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)
(责编:宋心蕊、赵光霞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