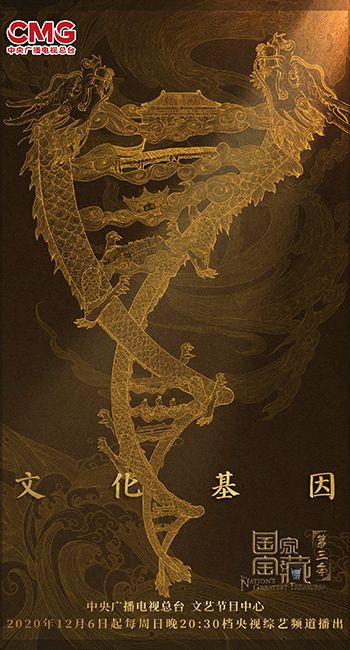划重点:
孙莉几乎每次排练都哭,哭到低血糖都犯了,直到排练中段,导演训练孙莉把外溢的情绪收起来。丈夫黄磊比她还着急,剧组偶尔放假,就催她背词,每天都要背一遍。
饰演卫生员的关皓天在家做了一次凉面,手擀的面条,配着菜码和调料搬到排练厅,倪大红吃了3碗,赞不绝口。趁着高兴,端着面条碗主创们拍了张大合影,王澜把照片上所有人的脸都P成了倪大红。
倪大红将进入这个剧组看作一种幸运。在写对这部戏的感想时,特意表示“谢谢你!雅伊尔先生……”为了表达由衷的敬意,他送了双潮鞋给导演,导演喜欢得不得了。
文/裴晨昕 编辑/向荣中文版《安魂曲》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当晚,1.6公里外的工人体育场正在进行北京国安和北京人和的京城德比。夏日天黑得晚,蓝灰色的云低垂,带着一丝雨意。剧场大厅里,观众热络地和宣传展板上的倪大红合影,有人高声讨论要不要提前离场,以躲避两个小时后,工体北路上可以预见的拥堵。剧场内,导演雅伊尔·舍曼和坐在前排的朋友打完招呼,就站在一楼观众席旁边的过道上,和工作人员闲谈。他背对着正在进场的观众,淹没在即将欣赏和评判他作品的人流中,直到全场压光,演出开始,剧场工作人员把他清出过道。天使摇晃着铃铛走过,倪大红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圆形舞台,用浑厚沙哑的声音念出全剧第一句台词:“我们的小镇泊普卡还不如乡下。镇上住着几个老人,却很少去死,小气吧啦的,让人不耐烦。”说着,他清了一下算盘。正是拨弄算盘的动作,让雅伊尔意识到,这部以色列著名话剧的中文版,可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——在他以色列的家里,算盘是挂在墙上的古董,他从没见过会打算盘的真人。看到倪大红手指翻飞拨弄算珠,他彻底震惊了。倪大红饰演的老人手中拿着算盘
中文版《安魂曲》筹备了5年,原作是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·列文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。2006年,原版在中国演出时一票难求。雅伊尔·舍曼年少时看过两次,就达到“改变了我的人生”的神奇效果。列文遗孀邀请他导演这部剧的中文版时,他连细节都没问就答应了。他不敢肯定这次改编能否获得大众意义上的成功。“因为我们看待成功的角度不一样。有时候完全相反。”他只希望“用我的语言,我的风格来导演话剧,让剧中带有我的签名。”1杜宁林刚拿到剧本时,没看出什么感觉。倪大红说这剧挺好的,可她还是犯嘀咕。排练一开始,她很快体会到了妙处。抠戏时,导演把希伯来语翻译成英文,执行导演再把英文翻译成中文。有时候,导演和执行导演还在掰扯,杜宁林看他们眼神就明白了,“我说这件事你不用说了,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。”雅伊尔年轻又强势,他将排练日程精确到小时,对每个演员都直率地提出批判和意见。“我离开了我的家,我的家人,我的朋友,我的工作,来到这里面对这个项目,我只有我的专业性。”他对《贵圈》说。演员是他亲自坐镇试戏选出来的,用制作人李淑俊的话说,都是一粒一粒淘出来的金子。选角第一天恰逢世界戏剧日,老戏骨杜宁林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去试戏,《安魂曲》招聘演员的文案,把这部剧说得太诱人,让她忍不住想试试。另外,“倪大红演老头,我想跟他交交手。”杜宁林与倪大红在《安魂曲》中合作
很多观众是冲着倪大红来的,保利剧院首演当天,中庭摆放的花篮中,有两个来自倪大红粉丝会。卖周边纪念品的长桌前,不时有小姑娘来问,几种环保袋和T恤衫,哪一个有倪大红在剧中的形象。凭借电视剧《都挺好》获得空前的国民热度后,倪大红没有乘胜追击,而是选择藏身于舞台,先后演了《银锭桥》《安魂曲》两部话剧。有朋友向杜宁林打听,倪大红排练是不是天天请假,“没有请过一天假,而且每天都是提前半小时到现场”,杜宁林说。雅伊尔第一天就立规矩:“如果彩排两点开始,我希望你们一点半就到”。在排练室要保持安静,手机一定要静音,在帘子后小声背台词也不可以,“因为帘子不隔音”。倪大红说,这就像是回到上大学那会儿,“在排练场里走动都不敢,甚至想把鞋脱了。”雅伊尔用5天拉完了15场戏,这是中国演员很少体会的强度。从技术上来说,背台词是最让人沮丧的部分。“如果你在排练的第一周就把台词背完了,再看时间表,就会觉得,哇,我还有一个半月可以雕琢我的角色。”雅伊尔说,他就是要“把绝望的部分往前挪”。倪大红饰演的老人承担全剧60%的台词。“只要你看到他眼神游离呆坐在那儿,就是在背台词。”李淑俊发现,倪大红练起台词就不管不顾。“红红老师你吃点什么呀?”“我不吃!”“红红老师你喝点什么呀?”“我不喝!”“那你需要什么呀?”“我就想背台词”。好几位演员在不同的场合告诉《贵圈》,剧场艺术是导演的孩子,某种程度上,演员也是导演的“道具”,他们非常努力想呈现出导演脑海中的《安魂曲》。雅伊尔是个人风格非常明显的导演,在以色列时因为深刻诠释列文的作品而受到推崇。他和杜宁林的儿子差不多大,却得到杜宁林无条件的尊重和信任,“有时候唱,有时候跳,有时候哭,有时候笑,没有问题,看导演要什么色彩。导演说你这再红一点,你这再绿一点,导演调。我都具备,这是演员。”排练初期,最“绝望”的是饰演妓女的温子墨和王澜。温子墨的压力来自反串,他焦虑得犯了肠炎。王澜要突破自己“亲和友善”的一贯形象去演妓女,也紧张得血压飙升。在朋友圈看到演员招募信息时,温子墨是想应聘醉汉的。第一句台词“走啊!”刚说完,就被导演打断:“你愿意试试妓女吗?”列文笔下的娼妓粗俗滑稽,肉体与精神完全分离,只把身体视为谋生工具。在面试了太多温和漂亮的女演员后,雅伊尔决定让男演员反串,“那种对身体的不在意,几乎是男性的本能。”再怎么焦虑,还得自己想办法。温子墨找演过女性的师兄取经,师兄建议他先通过外在找找状态。他冲到北舞外面的服装店,买了条黑色百褶裙,排练时一直穿着。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,上厕所时搂着裙子遮遮掩掩的。导演对他说,上了舞台是要面对更多观众的,你得突破。导演希望妓女展现出更多的力量感,王澜跑到公园,一边抽打树叶一边念“我就是喜欢干完那事以后吃完咸鱼”,去健身房举铁,一边默念台词一边和杠铃较劲,下课一看,肌肉都出来了。导演建议演员排练时找贴近角色感觉的服装。李晓强一进排练场,就把背心一穿,马绳一缠,瞬间入戏。“十单不如一棉,十棉不如一缠。”他告诉《贵圈》,这都来自生活经验。倪大红找来几双草鞋,还友情赞助了杜宁林一双,“杜杜,穿上草鞋就找到角色感觉了”。孙莉准备了一双小靴子,最初的设计中,她有大量的奔跑。《安魂曲》中传播最广的金句,几乎都是她的台词。一次联排中,她沉浸在角色丧子的悲痛中,背过身拧了一把鼻涕。“不许流鼻涕”,导演点评。她几乎每次排练都哭,哭到低血糖都犯了,直到排练中段,导演训练孙莉把外溢的情绪收起来。丈夫黄磊比她还着急,剧组偶尔放假,就催她背词,每天都要背一遍。孙莉饰演母亲
一周5天排练,从下午两点持续到晚上十点。演员提前半小时到,雅伊尔则会提前两小时。中以两国有6小时时差,以方团队常常会在深夜传来服装、音乐、舞美素材,雅伊尔不和演员坐在一起,戴着耳机,忙着和以色列团队沟通。排练间歇,中国演员说笑,他就在旁边看着,大家都笑了,他也不知道在笑什么。杜宁林觉得语言不通也很好,没有情感交流就不会厚此薄彼,反而让大家保持非常职业的状态。“职业”是个高标准,并非人人都敢以此自况。杜宁林只用一天,就练会了导演教她的希伯来语摇篮曲。李晓强为了模仿马啸,找到马车前进的节奏,每天回家后都在车库练两个小时。第一次联排结束,导演宣布放三天假,这把倪大红愁坏了:“三天,那不放凉了吗?跟导演商量一下,能不能就休息一天?”后来,他拉上李晓强和杜宁林,自己加练,李淑俊负责订饭。2排练的45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走出地铁口,顶着仲夏正午的毒辣阳光,62岁的杜宁林要穿过狭长的大石桥胡同。窄道两旁电缆交错,一根树枝都没有,只有遮阳伞撑出眼前的一方阴影。白色土狗慵懒地卧在墙边吐着舌头,小店门口的伙计打着瞌睡看店,住户窗台下晾着的红辣椒,似乎肉眼可见地在炙烤下变干变脆。一刻钟的路程拐三个弯,杜宁林终于走进排练厅。“我的天啊,我都觉得我快死了。”坐在排练厅旁的咖啡店,她攥着纸巾擦汗。杜宁林是剧组年龄最大的演员,比倪大红还大3岁。她在《安魂曲》中饰演老妇,一个在孩子死后便“背对这个世界”的家庭妇女,操劳一生缺乏慰藉,死亡成了一种解脱。杜宁林的“解脱”是踏进排练厅的一刻。“一看大家都在那儿,马上回血,你也神采飞扬。”杜宁林饰演老妇
“能不能让我稍微喘息一下?”连续拉了几小时的戏后,倪大红申请到半小时的缓冲时间。每次休息,大家会站在排练室门口的小院里,抽抽烟,聊两句天。《安魂曲》剧组驻扎的三号排练厅位于全总文工团大院,三层小楼粉刷着白漆,布满嫩绿色的爬山虎。这里隐蔽低调却卧虎藏龙。隔壁的录音棚Tweak Tone Labs因为小清新的门脸,常被误认为是咖啡厅,内部却拥有世界顶尖的录音、混音和母带处理设备,小野丽莎、莫文蔚、林宥嘉都在此录过专辑。院里还有鼓楼西剧院,被戏剧翻译家胡开奇称为“中国第三代小剧场新锐代表”。在这里,史航主持的朗读会定期举办,上一期的主题是“你可以孤单一会儿,但不许孤单太久”,嘉宾席里坐着范冰冰和李玉。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排练厅,制作人李淑俊 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”。 首先要交通便利,倪大红住石景山,孙莉住顺义,选址必须在“城里”才可能兼顾所有人。其次要够大,200平米的要求淘汰了近一半备选场地。李淑俊坚信“一个细节做不到位,可能都会导致剧目损失很多。”出于保密考虑,工作人员搬来出品方过往剧目的海报立宣,将排练厅的窗户严严实实遮住。烈日被挡在窗外,意外地达到降温效果。这个小院成了炎热夏天里的一方净土,身处其中,除了饰演马车夫的李晓强偶尔喊出的一嗓子,能听到的只有啾啾鸟叫与丝丝蝉鸣。排练渐入佳境,组里的零食也越来越多,从水果、零食到坚果,导演还第一次发现了奶茶的美妙。他开玩笑说,回到以色列要开一家奶茶店。饰演卫生员的关皓天在家做了一次凉面,手擀的面条,配着菜码和调料搬到排练厅,倪大红吃了3碗,赞不绝口。趁着高兴,端着面条碗主创们拍了张大合影,王澜把照片上所有人的脸都P成了倪大红。倪大红与主创们集体感受“奶茶的美妙”(图片来自微博)
气氛渐渐松弛,排练却越来越紧张。雅伊尔在以色列是表演学的客座教授,很多细节都亲自示范。演员也对自己要求严格。排练时如果戏演得顺,王澜的表情就会特别轻松,如果不顺利,各种丧都写在脸上。有一天她连着三遍都演不对,排练结束后,她没像以往那样留下聊天,和李淑俊说“帮我和导演说对不起,我刚才没风度”,就走了。导演要的她都明白,但是做到需要过程。李淑俊说,塑造妓女这个角色是比较受折磨的,“她这个坡是一个缓坡,所以就会很痛苦。”饰演天使的闪蓝桥是组里年纪最小的,他最喜欢在候场时看前辈们演戏,边看还边琢磨,要是自己演能怎么发挥。有时候要上场了,另外两位“天使”喊他,他才猛地反应过来。导演和老演员的交流就像神仙打架。“你觉得这句台词的动机是什么?”每当雅伊尔向倪大红发问或是指出细节处理上的意见,得到的多是一段不尴不尬的沉默。“他是紧张了吗?”“他明白吗?”“他不明白吗?”雅伊尔开始总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倪大红少有回应,总是沙哑着“嗯嗯”几声。“我每一次都会被他能那么深入地理解我的意思震惊。”雅伊尔感慨,“这是我想要的,但又绝对不是我预期看到的。”倪大红觉得,这样的过招让他受益匪浅,他将进入这个剧组看作一种幸运。在写对这部戏的感想时,特意表示“谢谢你!雅伊尔先生……”为了表达由衷的敬意,他送了双潮鞋给导演,导演喜欢得不得了。排练结束已是月上柳梢,演员们结伴走过白石桥胡同去坐地铁。杜宁林精神体力都有些透支,“和导演说完拜拜,明天见,这个时候就完蛋了,走地铁也走不回去,他们就拽着我。”闪蓝桥则很兴奋,既有交完作业的轻松,也有创作带来的快乐。有时导演也会加入,聊些排练厅里来不及充分交流的细节,也会聊聊以色列的房价和在中国的趣事。胡同里安静下来,路灯下偶尔有还没散的象棋局。他们的说笑,融化在温暖的夜色里。3带妆联排的第一天,温子墨脱下自备的黑色纱裙。这个角色,头上是1尺有余的冲天发型,脚下踩着8厘米高跟鞋——他本就瘦高的身形被拉得更长,晃晃悠悠地,在后台摔了一跤。当时是在调节舞台打光,演员们全副武装反复上场又退场,饰演胡瓜醉汉的演员王上斌从背景板后探出头——因为在试戏时唱了一段音乐剧《狮子王》选段,导演一直叫他辛巴。“Go back,Simba”“Simba go”“go”,拿着麦克风,雅伊尔冲着舞台大喊着。“辛巴”吓得像土拨鼠一样立刻把头缩了下去。剧院大门紧闭,层层帷幕高高悬起,将后台包裹在一片漆黑中。温子墨没看清前方悬着的一根绳索,被绊倒了,整个人摔在一块铁板上。在这之前他一直提心吊胆,担心摔跤,摔了这一下,反而踏实了。《安魂曲》灯光设计
临近首演,所有人都处在高度紧绷的状态里。雅伊尔在舞台和控制席间穿梭,严格把控着灯光、音响的每个细节。当晚的排练要延长两小时。每小时场地租金5000块,这意味着预算又要追加1万。进入合成周,面对不断超支的账单,李淑俊开始在导演和投资方之间斡旋。每一处打磨精进都意味着新的开销。五天内,剧组先是拉来一套音响设备,而后又运来了重达3吨的灯光升降梯。此外,为了更贴合演员个人特色,增强舞台效果,以色列的造型设计在看到演员后又对本已定稿的服装造型再次修改。“人家不是说制作人和导演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吗?导演肯定有他的艺术追求,但我肯定要考虑预算”。李淑俊不是没想过直接和导演说不。有一次,投资方提出“一定要跟导演连夜开会”,但当她站在观众席看到舞台时,还是选择了最大程度为导演争取空间。3月《安魂曲》早鸟票开售,一分钟就被抢光,观众的期待真切可感。得知此消息后,雅伊尔表情平静,“如果票卖得不好,我可能压力更大。因为我不想让演员们失望。当剧场是满座的时候,通常演员的发挥会更好,剧场里的能量也会更加强大。”所有的努力都为了最后呈现的舞台能达到完美状态, “如果你问我,对这部剧投入了多少,我会说我是全倾投入。”雅伊尔说,“就像我把血淋淋的心都押在桌上了。”来中国后,他专门去看了《恋爱的犀牛》,想知道中国观众在剧场中的表现,可以解构一部话剧到什么程度,什么样的隐喻他们能够理解。“最后呈现出最好的一切,那我都认了。”这段时间,李淑俊不停地在朋友圈刷到业内人士对《安魂曲》的期待,来自同行,来自前辈、晚辈,来自所有的人。人们说起今年最期待的戏,总会提到《安魂曲》中文版。每当看到这些,李淑俊就压力备增,连点赞都不敢,“我想等到17号再说,因为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”演员也感受到莫大的压力。温子墨和王澜的定妆照,一个高瘦,一个圆润,站在一起就像《灰姑娘》里后妈带来的两个姐姐。导演告诉他们,这是严肃戏剧大师的深刻作品,这两个人物有喜感却不能卡通化,要走心,要有真实感。为了实现这样的真实,温子墨从最初模仿女性的肢体动作,转而从内心去理解角色。微博里翻到艺妓的爱情故事,他就融合到角色对梦中情人的想象中。温子墨(右一)和王澜(右二)饰演妓女
《安魂曲》中三个承受着死亡和悲伤的故事,一个比一个绝望。角色的悲剧也刺激着演员。杜宁林每天拍完戏,尽量回家就放空。“就不能想,一想就演不了了。”心里说不想,可是还是不行,越排斥越近,越推越近,“每一根汗毛孔都沉浸在这里面了。”李晓强每次出场都在模拟马车前进时的颠簸状态,踢着高抬腿,汗一身一身的出。前几次联排,导演都没有给他具体的指导,只是说“特别好”,这让他十分不安。试戏时,导演本来希望他演更具“喜剧感”的醉汉,但李晓强是奔着车夫来的。车夫的原型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《苦恼》:独子因病离世,满腹苦痛,来来往往的客人却没有一个肯驻足聆听,他只能对着自己的马倾诉。年轻时,李晓强在伊犁当过兵,在兵团农场拉庄稼,赶马车,到河里游泳,把自己晒得黑黑的。他也有许多“对父母不能说的,对老婆孩子不能说的话,只能自己生扛”。他第一次读契诃夫小说时,便被这个角色打动,“我很理解他,事不一样,但是情绪是一样的,苦恼是一样的。”倪大红分享过雅伊尔对这部剧的解读:“就像一个蚂蚁窝的一群蚂蚁,都在做着各自的工作,如果有的蚂蚁死了,蚂蚁死了就死了吧。我们的状态就是蚂蚁,或者是把它的尸体拖回去,继续忙碌着,工作着。没有看到他们那样子的悲伤,不是说没有悲伤,只是没有看到那样子的悲伤。”角色定妆照前发布前,工作人员找到演员,希望每个人说说自己的感悟,在收集来的13段话中,提及死亡的有10处,“生”则有22处。戏里戏外,每个人都试图在悲剧的表象外,捕捉到更内核的一点希望。雅伊尔一直试图让演员体会到“每一个悲剧的故事后都还有一点希望”,起初王澜并不能理解,“希望到底是什么”,后来她终于悟出,“你活着,就拥有选择的权利。你活着,就能看见希望的曙光。”47月17日《安魂曲》首演时,灯光和音响设备先后出现瑕疵,部分演员的表现也不在巅峰状态。台下观众的反应不如预期中热烈。第二天,豆瓣评分出现,比以色列原版低了很多。首演的效果让此前看过联排的人感到意外。每个星期五,剧组都会进行一次联排,第四次联排结束后,李淑俊克制不住激动,在群里抒发了对各位演员的感谢。本来聊美食聊得热火朝天的群一下子安静了。1分钟之后,倪大红说,“俊姐,我们在聊火锅呢。”第五次联排后,李淑俊组织大家去吃了一顿小龙虾。导演在餐桌上说了好多话,聊得特别感性。孙莉喝了很多红酒,认真地表白,“好爱导演啊。”7月6日排练结束后的合照(图片来自微博)
李淑俊说,这些专业的舞台剧演员都希望去演好戏,希望获得更多技术上的成就和收获。导演恰好给了他们这些东西。倪大红也说,排这个戏,他就像一个海绵,不断吸满了水再排干,再吸满再排干,如同一场甜蜜的折磨。首演谢幕时,演员、导演和幕后团队共同站在台上,迎接观众的掌声。接下来的5个月里,他们将在12个城市的30多个夜晚不断上演。那一刻,他们仿佛回到45天前,鼓楼西剧场的排练厅内,剧组第一次进行剧本围读。中方演员、以方团队,二十多人围坐在由6张长条木桌拼起来的会议区。制作方、出品方的工作人员也捧着剧本旁听。窗外白墙藤蔓缠绕,爬山虎的叶片重重叠叠,随着微风扑簌簌地摆动着。读剧本时,雅伊尔有些紧张,之前以色列团队和中方制作人有不少分歧,第二天团队要回国,冲突还没解决。围读结束后,他发现有人激动得流泪,“他们听到中国演员读台词,发现他们那么投入”。在那一刻,紧张的气氛消失了,这个跨越国界、直指人性的话剧,有了一个美妙的开端。